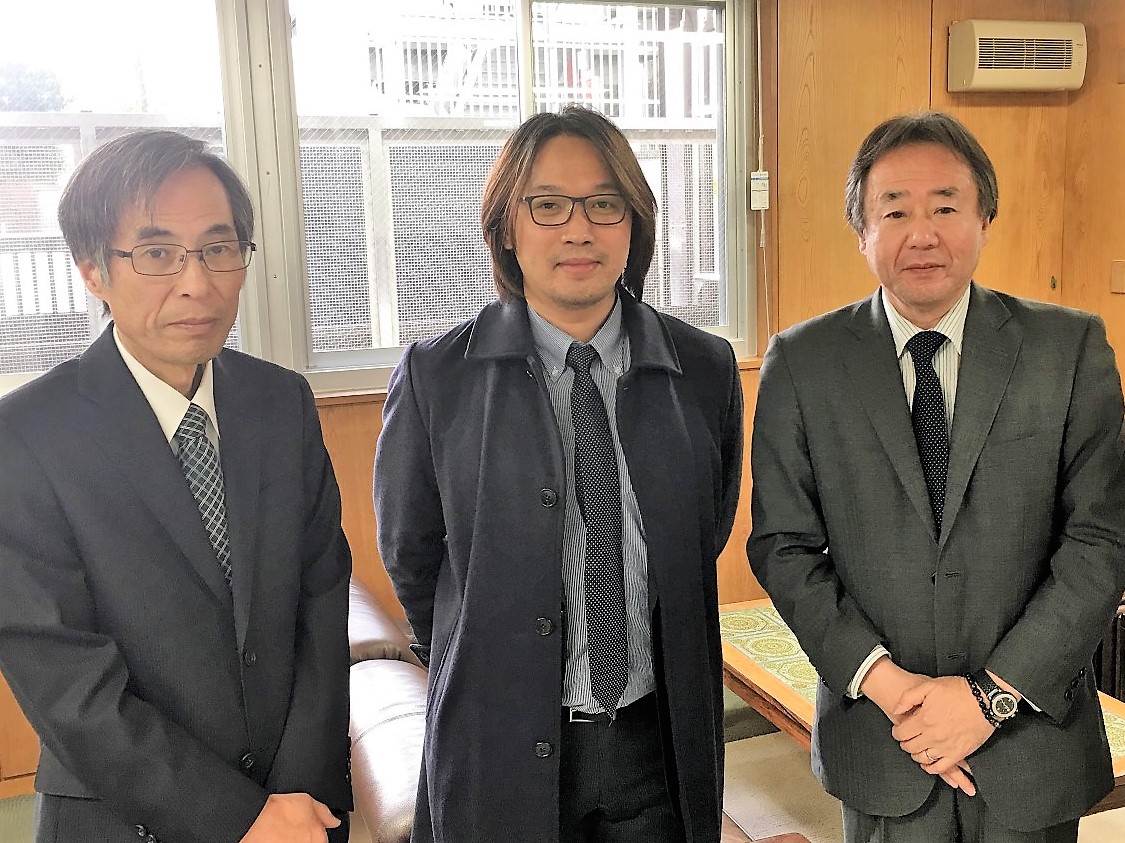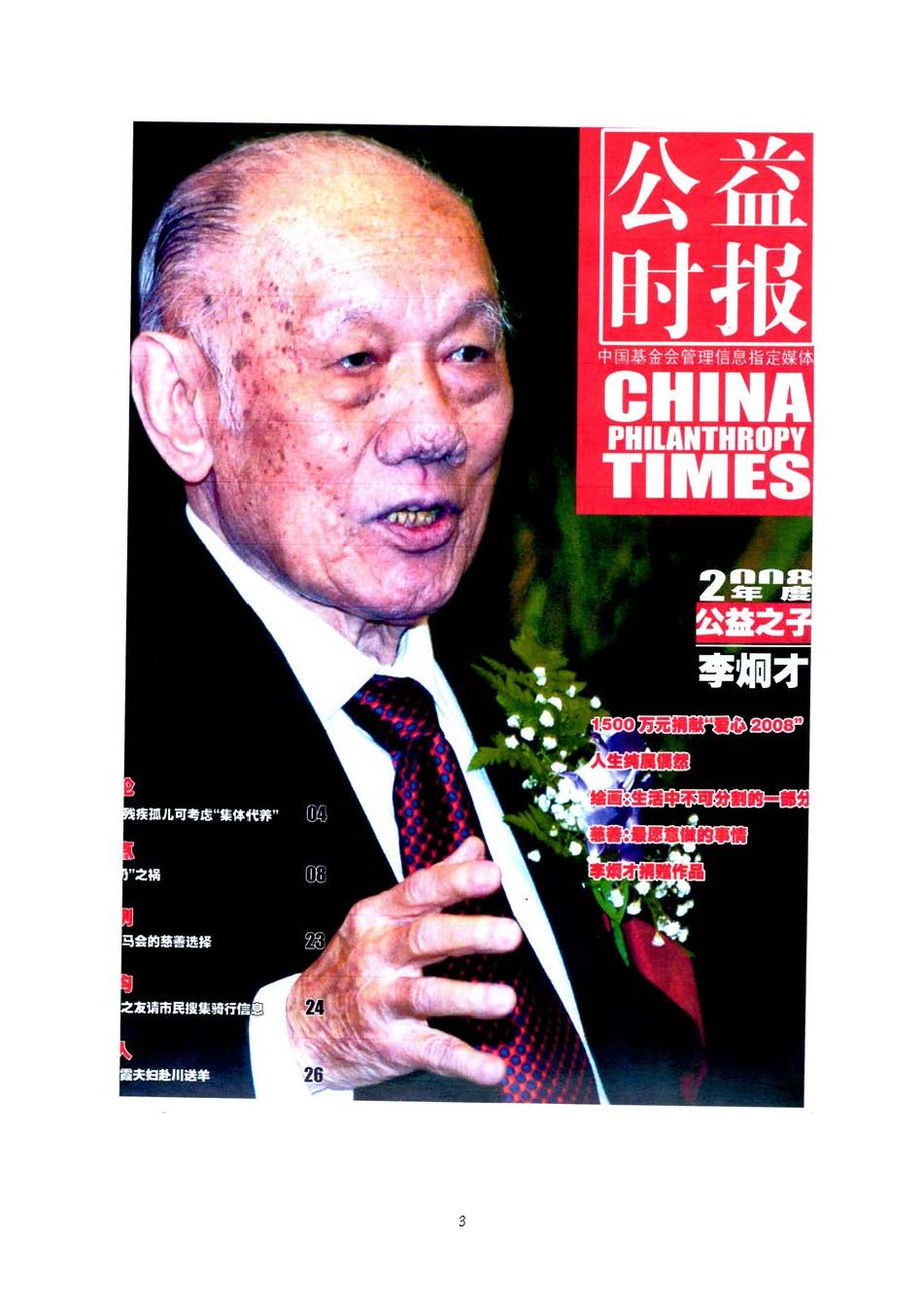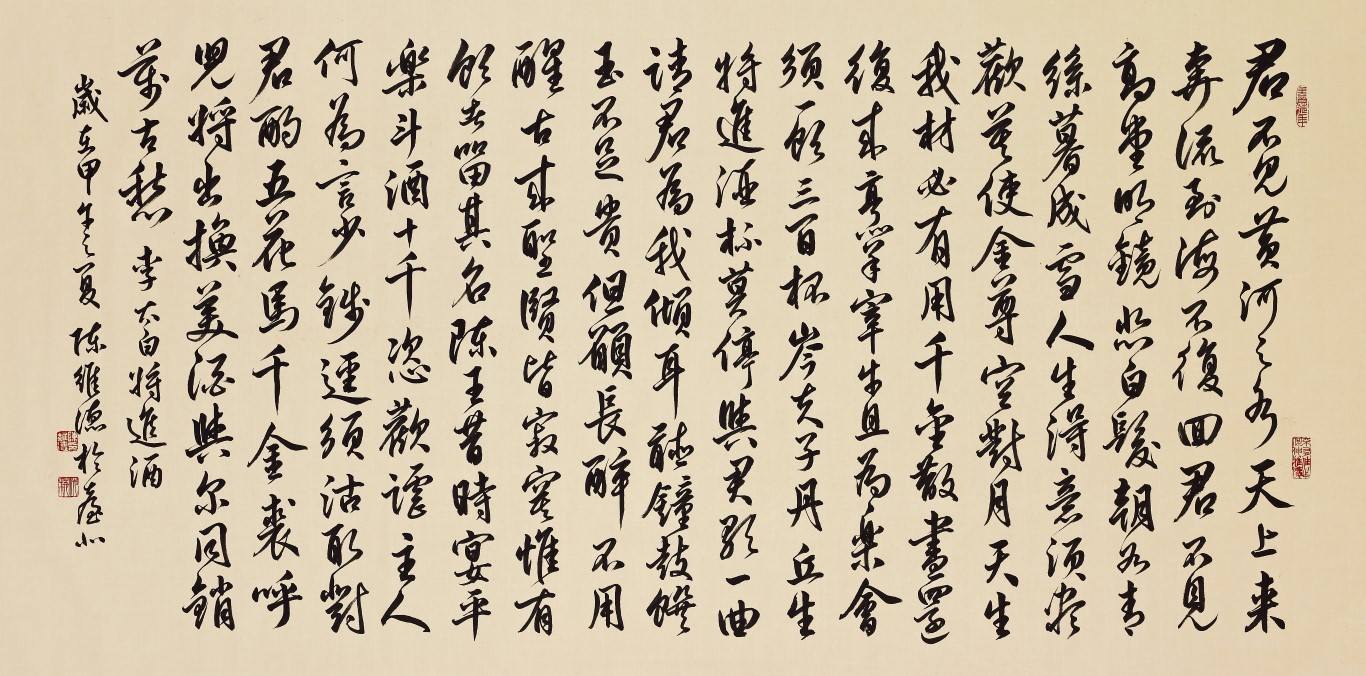歸國旋即南下高雄佛光山總本山,雖說是總本山,亦不過是佛光山舊院,接待者為一老法師,接引我等進入萬壽園 星雲長老佛事處,問訊、獻花、頂禮三次,轉移至座位,與僧俗二眾同聲輕誦: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、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、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」
一邊默誦、一邊靜坐思維過往與佛光山等因緣,隨即浮現心識之中,十餘歲時隨家母常於佛光山當義工等事,爾後又於2007年11月4日於佛光山 得戒和尚 星雲大師座下受菩薩戒。長老49年渡台,受到台灣諸多貴族、士紳、受刑人、政治犯、思想犯等尊敬,不是沒有原因。若按世俗一般企業比擬,佛光山已經算是世界級企業了,全世界遍及道場三、四百所,然長老佛事處大小規模與一般俗人後事無異,簡單素雅,我看都比一般人還簡單。
舍利者,乃是一種對於過往弘揚佛法傳布之精神所在而感懷。若是對於其產生了執取則會演變成為執世俗法為實有不變易法,然世俗法皆會有變異,如供養舍利之增生亦為世俗法,有增生故。若真實對其產生了執取,則已經失去對佛法學習之意義,我們學佛乃根據異生自身情況而做轉變習氣改變,並不是崇拜一物而作為究竟,然若有一物可藉相觀心,何不為之?學人應當以法舍利為依止,所謂三藏十二部諸經論。除三藏外,亦以長老全集為參酌,如此方為真實仰信佛教之行者。
《菩薩地持經》云:「尸羅波羅蜜菩薩種性相者,是菩薩身口意業性自柔軟,不增惡行,不樂煞生。設作惡業,心生慚愧,能疾悔除,不令增長。不以刀杖恐怖眾生,體性仁賢,常懷慈愛。恭敬尊長,奉迎供養。善知機宜,所作巧便,善隨人心。言常含笑,舒顏平視,先意問訊。知恩報恩,所求正直,不偽不曲。受如法財,不為非法。性常喜樂修諸福德,見人修福尚以身助,況復自為。若有眾生更相殘害,打縛割截,毀訾呵責,有如是等無量眾苦,若見若聞,心常憐愍。重今世善及後世樂。於輕罪中,心常恐怖,況餘重惡,而不畏慎。若見他人農商放牧、書數算計、和合諍訟、求財守護、出息施與、婚姻集會,如是一切如法事中,悉與同事。鬥亂諍訟,互相恐怖,若自若他,無義無益,如是一切,不與同事。善能遮制十不善道。若為他使,隨順其教,己所宜行,諮訪明哲。於諸事業,廢我成彼。常懷悲惻,不興怒害,設令暫起,尋即除滅。恒修實語,不誑眾生,不離他親及無義語。言常柔軟,無有麤惡,於己僮僕尚不麤言,況於他人。於諸功德,心常愛樂,見人行者,隨喜讚善。如是等比,是名尸羅波羅蜜菩薩種性相。」
數小時候,大眾共同做了晚課。走出來佛事處,老法師隨手給我一袋素食,四大顆油炸麻糬球,她說看我氣質非凡,見我坐姿堅固數小時,對於佛法很有信心,是故給我一袋素食,讓我回去車上吃。法師實在過謙我,我哪裡氣質非凡,佛事處,見諸老菩薩,有的頗腳了、有的老的走不太動需要人扶持、有的看起來就知道是做苦力勞工的卻隻身前來讚頌,而我一男人身,卻不如她們的發心,我若是頗腳、需要人扶持、做苦力收入不豐者,能像這些老少菩薩們如此嗎?實在慚愧。
長老所安奉處:萬壽園是什麼?如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〈我創辦社會事業的因緣〉中所云:「在佛光山,我們設有一個萬壽園公墓,除了提供骨灰安奉外,還在萬壽園設立了六個安寧病房、六個祭祀的廳堂。安寧病房的設置,我想到人到了最後階段,假如有眷屬跟他一起同住在安寧病房裡,他會感到比較安心、安慰,因此,我們在安寧病房裡,設有眷屬居住、飲食吃飯的地方。在安寧病房裡,曾經有人像住在療養院一樣,本來是等待往生的,後來竟然恢復健康,活著回家了。所以,一個人對生死能放得開、看得開,生也好、死也好,生死其實都是一如也。
我設立萬壽園公墓,大約是在一九七六年左右,當時佛光山開山十週年了,高雄縣政府給了我千萬個難題,這當中許多原因很複雜,我也無法一一述說,只能說為了要領到佛光山寺廟登記的執照,也就不去計較,努力跑相關單位辦理證照。」
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3〈有關宗教法答問〉又說:「以佛光山為例,山上的萬壽園,主要是提供給信徒、佛光會員和徒眾及其父母往生之後的服務設施,也捐出兩千個龕位,免費讓貧寒者放置使用,或照顧孤苦無依者。」《佛教叢書》27〈人間佛教的社會慈善事業〉:「今日佛光山萬壽園公墓也為孤苦無依者,免費提供——『最後的歸處』。」
萬壽園有哪些佛弟子於此?該文後又云:「除了我的母親李劉玉英外,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、陳誠副總統暨夫人譚祥女士、三湘才子張劍芬、佛學名教授楊白衣、方倫、名作家卜少夫、《中華日報》駐華府特派員續伯雄、新聞界大老歐陽醇等。」
孫張清揚女士何許人也?如《佛教叢書》28〈人間佛教的奉行者〉云:「台灣佛教今日的蓬勃發展,孫夫人的勞苦功高,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然而自從因孫立人將軍事件隱居以後,人情的澆薄現實令人唏噓不已,年老之後,更是無人問候。我有感於他一生護法衛教,功不可沒,因此經常去探望他。臨終前,他將永和的自家住宅付託給我,言明作為佛教文化之用。往生之後,我雖知他有兒有女,但還是自願為他付喪葬費用,並且將他的靈骨送往佛光山安厝在萬壽園內。現在,我計劃改建他的故宅,作為佛教文化的重鎮,以紀念他一生推行『人間佛教』的貢獻。」
除了孤苦無依者、佛教徒之外,萬壽園亦奉安台灣二二八事件受難者,如大師《佛教叢書》28〈二二八的平正〉云:「一九四九年初到台灣來,我就聽說『二二八事件』,心裡一直很想為同胞們作些什麼,來化解這段歷史的悲劇。所以,三十多年以前,我曾建議政府有關單位為『二二八事件』中的死難同胞予以平正,直到一九九一年,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成立不久,在因緣具足的情況下,才得以一償夙願,首次發起『佛力平正二二八死難同胞慰靈法會』,邀請政府官員、民意代表、受難家屬同來參加,並且受理登記,將受難者遺骨奉安在佛光山萬壽園,定期上香祭拜,意在藉此消弭過去的裂痕,喚起社會大眾共識,將歷史的教訓化為和平的力量,從而共創一個互助互重,富麗安樂的社會。」
顯見大師最後選擇萬壽園作為安葬處,亦有其意義所在。